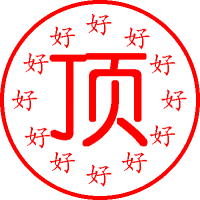标题:一花一世界 一盘棋里窥见文人性情
一朵花可窥世界万千变化,一盘棋也可窥文人性情。
只当了六个月短命宰相的诗人元稹,他的人品向来不为人所称道,只从下棋中就可看出来。他酷爱下棋,棋输时却喜耍赖。《棋天洞览》记载,“元稹与李杓直棋,稹已败,乃窃杓直数子咽之。”败局已定,为要面子,元稹竟将李杓直的数枚棋子放在口中。
三国魏时的阮籍与朋友下棋之时,家人跑来送信,告知阮母去世。朋友丢棋欲走,可阮籍坚决不干,非拉着下完不可,可谓“善始善终”的典范,但不能说他对母亲没有感情,之后他狂饮酒三斗,大哭不止,吐血数升,体重骤减。
由阮籍我忽然想到梁实秋先生,梁先生也是棋瘾奇大,作有妙文《下棋》,阐述下棋之道,头头是道,实是他有亲身体验。据梁实秋之女梁文茜回忆,说父亲的两个爱好,一个是吃,一个是下棋。当年梁实秋得知闻一多被暗杀时,正在与朋友下棋,义愤填膺,拳击棋盘,一只棋子掉到破地板缝里,再也没有抠出来。
阮籍与梁实秋下棋时闻听噩耗,一个如湖水表面平静,一个似火山当场喷发,形式不同,但真心同出一源。
人生如棋,棋如人生,每一步都透露出人的性情
对于文人来说,棋是智力体操,棋是艺术,更是一种哲学和人生态度。
梁实秋先生《下棋》中开篇说:“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棋,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。杀死他一大块,或是抽了他一个车,他神色自若,不动火,不生气,好像是无关痛痒,使得你觉得索然无味。”但他又说:“有一面下棋一面诮骂者,更不幸的是争的范围超出棋盘,而拳脚交加,为此下棋的意义完全被忽略了”,梁实秋在棋中阐述了一种“不能无争,也不能争得超出范围”的人生态度,一种高品位的人生境界:做任何事情不认真不行,太认真也不行。
阿城的《棋王》讲了一个舍棋之外再无它物的棋呆子的故事。故事的背景是那个精神匮乏的混乱时代,“棋呆子”王一生除了吃饭就是下棋,他钻研棋艺,渐至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,在全县象棋比赛之后以“盲棋”大战九大高手。人性在受到压迫的状态下,反而呈现出令人惊异的具有力度的美感:“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,瞪眼看着我们,双手支在膝上,铁铸一个细树椿,似无所见,似无所闻。高高的一盏电灯,暗暗地照在他脸上,眼睛深陷进去,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,茫茫宇宙。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,久久不散,又慢慢弥漫开来,灼得人脸热……”
有人问阿城,写那篇《棋王》到底想说什么。阿城淡淡的吐出一个字:禅。
其实,阿城完全可以一个字也不回答的,一个淡淡的微笑就够了。
按说,这样会写下棋的作家,棋一定下得不错,但2004年阿城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:“其实,我的棋很臭,不太会下,和王一生可差远了!”不知是不是自谦之辞。
作家李洁非在《说“点三三”》中谈到下棋与文学创作,说点三三本是围棋的一招,即在“当对方在角上占星位而与其它子粒之配合并不严密时,三三一点,必活一块”,而李洁非将鲁迅的那些短小杂文,也比作点三三,“不多么唬人的阵势”,鲁迅胸有成竹地出其不意地“只管往三三上一点,立教其虎皮羊质的原形毕现”,这个比喻,非有对围棋较深的理解和造诣,是想不出的。(文/陈雄)